尘世,那些叶子立着在杯底,不肯倒下。我寻觅可以形容她们这种立的词语,或直立、或矗立,又或屹立,却没有找到更好的那一个词。我知道,那种立已是一种态度,一种执着,或更像一种偏执,即使片刻也要将一种自以为的美坚持,形如女人。我看着这些叶子舞蹈,一种以可以让你看清时光流逝的舞,一种由天际飘落尘世般的绝尘之舞
天道,茫茫。鬼道,苍苍。魔道,何为魔道?雨里行走的人不断的回头,为何却越行越远?一个女人在雨夜里梦呓,却为何喊的偏要是他的名字?尘世,不分天道、鬼道、魔道,这一世,所有的道都将在我的世界又再虚幻。这一生,我的路上,轮回的因果注定你我生生的不得相见,只得相念。记得吗?在家乡,那一种花,便是如此。花开的
“你走开!我不要再见到你!”女人哭泣,推搡着眼前的男人,尽管他很想将她拥抱在怀里,可她说她厌恶他这样。男人默默的走开,打开房门,回头看看自己歇斯底里的女人,离去。“我错了吗?我其实真的要他这样离开吗?”女人问自己,坐在沙发上抽噎着,茫然着。其实这一切不过就是自己男人为一个女人写了一篇文章,不过就是自
读史,享受尘世间的寂静。窗外的苦楝树伸臂遮住晃眼的日光,只为了由人享尽这尘世间的寂和静。一壶茶摆放在几案。掩卷闭目,谁的影对我欲说还休?任由那前世的惆怅沉降,沉降于茶,沉降于影,沉降到我再也找寻不到你红唇的吻痕。尘世间有人鄙视这卿卿我我的文,却又沉溺在这卿卿我我情,不得自拔。茶许多时后,没有了温度。
妻,你如茶,盛开在我那心灵深处的青绿浅红,浸染了我灵魂世界的宁静与快乐。我凝神那盏茶,端详那血色的红,妻的影子路过那红,红即在那瞬间黯然。我举起杯,让那红跟随妻的身影,我喜欢那暗红之后的影,佛说那是我前世的埋骨人。埋我骨的前世的女人,你或者只是尘世里最平凡的女人,但我却看到你掩埋我时,朝霞在你的脸颊
8曰30日,雨。这是一天之晨。这一天之晨的尘世弥漫着秋雨的秋思,除了雨声,除了键盘的敲击声,尘世一切沉寂。空白的屏幕,我向你倾诉,你也需沉寂,沉寂如水。当你沉寂如水时,你或者可以在那一片雨痕之后,看到那一片云纯净、无暇的就在你的心底。一个女人说自己老去,三十年的岁月可以无声的记录尘世的一切,而后又将
凡尘,湛蓝的湖,曼妙婀娜用以形容她的躯体。记忆里,在这一个季节、这一天,她的灵魂和躯体归属于了他,她是仙女,天上的织女。我仰头看漆黑的夜空,寻找那一只去向天际的喜鹊。记得早晨的时候我还听见它的啼叫,告诉我今天的夜里,牛郎要带着他的孩子去见心仪的女人,我祝福他,也祝福她。而我的妻子,在起床的时候,我吻
快乐,尘世里每一个人祝福别人最多的,每一个人心底不会虚伪推辞的。然而,那女人,你快乐吗?一阵风,刮在人间。一阵雨,浇不透这一季的炙热。“我有我的苦楝树,这阳光隔离于彼。”男人平淡而言,对于许多,他想要讥诮,却发现原来平淡里找不到更多的词汇去形容谁,去诋毁谁。“我是作家。”从太阳的那方,一个男人携着无
回头没有路转身向前走男人看不到女人的世界,温柔触不到那哀伤的壳。吹笛子的放下笛子,看着晨风里的鸟,告诉女人那才是快乐。女人轻轻走到他的身后,紧紧抱着这刚刚离开自己蚕丝被的男人,却知道这拥抱抱不住他那离开的心。“告诉我,你爱我。”女人的唇碰到男人的耳垂,轻轻的咬。男人笑着掰开她的指,转过身,告诉她说自
晨风,不再冷。其实走过了那样的夜,也只是走过。吹吹风,看看远山日出的景致,我还活着,这是我最庆幸的。于是,我还将要继续我活着的那些日子,如上班、如喝茶。我把日子定义成生死,也把你定义成遗忘或者曾经。我也希望你如此,或者你也该如此去定义你的那些个他或者她,我不能为任何人去确定任何一件事,上帝也不能。我
这是一个摆放花瓶的座子,制作它的人没有署上年月或者姓名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拥有这座子的第几个人。顺着岁月向上溯源,我顶多知道母亲拥有过它,外公拥有过它,而别的人是否还曾拥有它就不得而知。至于用它真正来摆放花瓶,或者只有外公,而他则由于那场革命使我不曾见到过他。但现在我却拥有着他留下的那花瓶座子。对于那座
人在旅途是一件荒凉的事情,厌倦了旅途的人才懂得温馨的可贵。我从旅途停下,停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旅途向左,尘世的诱惑布满权利的土壤;向右,尘世的风景长满傲慢的玫瑰;向后,即使没有见过上帝的我也知道,尘世的道路焉能回头?既不能回头,人生便注定平平淡淡的一路走去。“如果不平淡,又当如何?”“不平淡?那么无非
夜,在病痛中呻吟的妻无法入眠,窗外那棵苦楝树在路灯的光芒里依然的青青郁郁。尘世不为谁改变,守候着那女人的自己也不为尘世的谁改变,一由所有该来的来,该去的去,只静静的守候着那女人,微笑的看着那女人,倒一杯水,将那包裹在胶囊里的药丸喂入她的口里。“你也休息下,我疼得厉害的时候再叫你。”妻的眼关怀、柔情,
晨曦,昨日的可以吗?女人沿着鱼池,捻碎了手中的饼子,将碎屑顺着垂下的手轻轻的由它们飘落在鱼池,看着鱼池里那些宛若舞者的鲤围绕着那些碎屑盘旋、舞蹈,她以为那是最美。我要留这美在晨曦,女人静静的说。纤细的指缝,饼子的碎屑飘落,槐树的叶飘落。女人寻找昨日的晨曦。她说,就在那晨曦的拥抱里,他冷冷的背影忘记了
夜归,醒,妻、女已经在晨曦里远去。我知道最最不可耽搁的依旧是小涂的学业,知道这时的我于妻来说,已可放下。于是无奈,于是摇头,披衣下床,带着她临走的嘱咐和轻轻的一吻,依旧刷锅、洗碗,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人不能闲,正如此时,我闲下来便想起昨日的茶聚,想起缘之园许多散漫于记忆中那些个茶的韵。对于茶,我想起这
刷锅、洗碗,将所有的琐碎变成自己想要的宁静。小涂和她妈妈早早的离开家,那个一年级的孩子无可奈何的在这个暑假也享受不了自己的快乐。而作为她的家人,我们也已经很久没有共同的郊游或者午后的漫步,这是一种遗憾,也成为一种向往。“爸爸,我好累,为什么暑假我也不能休息?”某一天,小涂靠在我的怀里,问。“宝贝,没
尘烟,飘浮于杯间。舞蹈的是谁?那一盏琉璃盛满的翠又为谁?整个午后,我轻轻的将你拥抱,静静的爱,细细的品。这里,只有你和我。三十又七载的岁月,脚印被这一汪清泉洗尽。我孤独的走,越走,越孤独,最后只剩下这一杯的新翠,只剩下这一片舞动的叶,在水里,静静的旋,静静的转,静静的只为我舞出前世五百年的寂寞。你可
央宗嘉措沉寂了,将见与不见留在尘世间之后,他选择沉寂。如那块沉寂的普洱。“你见或者不见我,我就在那里,不悲不喜。”我读着央宗嘉措的第一句。这是什么?为什么有那饮过的那茶留在脑海的似曾相识?我问,我记忆佛祖那不来不去、不净不垢、不明不灭,我想起那茶不浓不淡、不苦不涩,你喝不喝,他都是如此。央宗嘉措一定
有一个女人,她是快乐的。快乐在于夜半的时候,她可以将腿压在另外一个男人身上。记不起有多久没有提到幸福两个字了。没人提,我自己也不去提,说出来的不见得是真的,得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。我曾经为自己沏一壶茶,看着房前苦楝树青翠而繁茂的枝叶,品味幸福的真谛。茶淡了,阳光也淡了,在天际不知疲惫掠过来掠过去的鸟雀
尘土,飞扬。没有风,清扬。茶香在细雨中冷凝。尘飞扬,在你回眸的那缕阳光后。风,清扬,你已看不见这一瞬间的雨,我在雨里独自寂和静,茶香冷凝。这茶香冷凝,遥遥,你在北方,不能共杯。由此,这雨更显寂寞的美。红尘红颜你笑靥如花,花开时,我不期花落,在我生命划过天际的夜空时,花不开不落。我爱你如花,醉你如茶。
 三角洲行动测试资格查询指南 手把手教你获取资格
三角洲行动测试资格查询指南 手把手教你获取资格
 解约金6500万!西媒:巴萨希望说服凯恩明夏加盟,尽管他薪水很高
解约金6500万!西媒:巴萨希望说服凯恩明夏加盟,尽管他薪水很高
 荒野乱斗官网入口在哪 最新官网网址速览
荒野乱斗官网入口在哪 最新官网网址速览
 小米17 Pro Max屏幕领先行业:京东方和维信诺陆续跟进
小米17 Pro Max屏幕领先行业:京东方和维信诺陆续跟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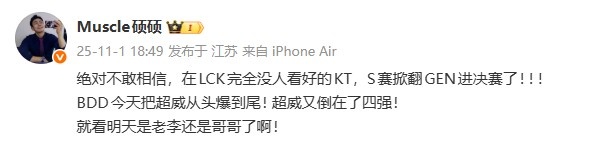 解说硕硕:BDD今天把超威从头爆到尾!超威又倒在了四强!!
解说硕硕:BDD今天把超威从头爆到尾!超威又倒在了四强!!
 蓝天云盘app怎么开通会员
蓝天云盘app怎么开通会员
 深情至极的唯美句子(精选69句)
深情至极的唯美句子(精选69句)
 地下城与领主手游官网入口在哪 最新地址一键获取
地下城与领主手游官网入口在哪 最新地址一键获取
 解约金6500万!西媒:巴萨希望说服凯恩明夏加盟,尽管他薪水很高
解约金6500万!西媒:巴萨希望说服凯恩明夏加盟,尽管他薪水很高